摘要:作为最早成熟的中国戏曲样式,南戏源自东南沿海乡村的“村坊小曲”“里巷歌谣”,富于浓郁的民间色彩,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极为强烈,具有鲜明的在场性。然而,囿于传统知识分子立场以及早期史料的湮没无闻,南戏的戏曲史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学界低估与遮蔽。将南戏视为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主要基于其产生的时间点与逻辑性、受众的多元性与通俗性、流布空间的广泛性、剧目众多与体制完备、演出的在场性与民间狂欢性以及对后世戏曲影响的广泛性与持久性等六大指标做出的判断。
关键词:南戏;民间艺术;遮蔽与磨光;艺术史生成规律
作者简介
刘祯:内蒙古鄂托克旗人,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和旅游部梅兰芳纪念馆研究员,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焦振文:河北涿州人,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
中国戏曲晚熟,从先秦萌芽孕育,至隋唐五代不断融合完善,最终在宋元之际成熟并形成戏曲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自此,中国戏曲高峰迭起,薪火相传,成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传世剧目最多、生命力最为顽强的样式”。[1]
回溯中国戏曲史,究竟哪里是其发展的第一座高峰呢?学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定为元杂剧。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1近世以降,持此观点者更是不乏其人。比如,廖辅叔认为:“戏曲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杂剧的特点和它的发展情况:元杂剧是一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综合了我国文艺词曲、歌舞、说唱以至舞台艺术的成果,放出了从所未有的奇花。但是元杂剧之所以可贵,主要还不在于它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3]廖奔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元杂剧在北半部中国赫然崛起,蔚为一代壮观!”[4]吕薇芬认为“这(元杂剧)是我国戏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却产生一批不朽的作品……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戏曲黄金时期”。[5]麻国钧等编著的《剧种·剧目·剧人》认为:“元杂剧是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6]郑传寅指出:“中国戏曲的繁荣却与‘覆盆不照太阳晖’的黑暗和灾荒频仍、瘟疫流行的贫弱相伴。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元代前期。”[7]此外,杜桂萍也认为:“随着明清两代传奇戏曲创作和演出的繁荣,早熟的元曲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必须担当‘戏剧典范’与‘文学遗产’的双重功能。”[8]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当诸多学者异口同声认定元杂剧为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时,恐怕囿于传统知识分子立场以及早期南戏的湮没无闻而低估了南戏的历史地位。纵观中国戏曲史,作为“小传统”的、民间色彩极强的南戏不容小觑,我们认为它堪称中国戏曲发展的首峰。
一、囿于传统评价标准,南戏长期湮没无闻
中国古代以诗文为正统,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被视为小道,为士大夫所不齿。学问正统、经史子集,研究和评价范畴也囿于此间。民间文艺作为“小传统”始终难入堂奥,民间戏曲更是卑贱至极。诚如鲁迅所言:“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9]自古以来,文人无论是染指戏曲创作,还是品评戏曲,多是以传统的诗文视角予以观照:或强调其义理辞章的结构章法,或强调文以载道的高台教化之功,或重视其意境文采的艺术呈现。无论是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还是吕天成将“意境”说引入戏曲批评,无论是金圣叹以“笔法”评点《西厢记》,还是李渔主张的“结构第一”,无不来源于文学理论。近代以降,王国维更是以文学的视角来批评戏曲:“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谓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2]98
诗文正统观直接导致了土生土长、俚俗粗陋的南戏不见载于文献典籍。诚如徐渭所言:“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10]239另外,明代何元朗也说:“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既不喜,则习者亦见少。而《西厢记》《琵琶记》传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独此二家。”[11]38由此不难看出,大量的南戏作品很可能因为“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和“士大夫耻留心词曲”而湮没无闻。然而,更糟糕的则是,士大夫文人还对那些土生土长、俚俗粗陋的民间戏曲采取一种蔑视甚至仇视的态度,这当中亦不乏专门从事戏曲创作和批评的人——包括明代的汤显祖、吕天成以及祁彪佳等,他们在论及弋阳腔等民间戏曲时亦大加挞伐,完全持否定态度。伴随着戏曲的产生,历代封建政府的禁戏之令便未曾中断。今天我们对早期南戏、弋阳诸腔及民间小戏的认知,更多的是借助于历代禁毁戏曲以及文人批判戏曲的文献,才得以窥探其一鳞半爪。
作为正统势力,正统文人对戏曲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戏曲被正统文人认可大致经历了“否认戏曲—批判戏曲—肯定昆曲传奇(文人)—描述京剧与地方戏—承认民间戏曲”这样的进化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戏曲逐渐从文学史中独立出来,以致有了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为代表的专门的中国戏曲史著作。即便如此,被认可的主要还是以元杂剧和明清雅部传奇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文学性的文人之作,而像南戏、花部乱弹等民间戏曲,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其《中国戏剧史》中说:“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至今约有百年的历史,其视点主要是关注宫廷和青楼歌坊的艺人演员们表演的城市戏剧,而从未关注过农村戏剧。”[12]再比如,张燕瑾指出:“宋代南戏还很孱弱,成就没有元杂剧高,影响不及元杂剧大。”[13]这里所谓的“孱弱”,不是戏曲演出本身不够规模,没有力量,而是南戏在“史官”眼里没有分量,处于“孱弱”状态。由此不难看出,戏曲的民间性被忽视,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使得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样式之一——南戏湮没无闻,成为中国戏曲史研究“一个失去了的环节”,[14]也导致了南戏在今天戏曲史坐标上的评估不足。
二、百余年来南戏文献的发现与历史描述
20世纪以来,较早论述南戏源流的当推王国维。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总而计之,则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于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几当全数之半;而北曲之出于古曲者,不过能举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渊源之古也。”[2]67同时,王国维还坚定地指出“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2]56足见王氏对南戏还是评价颇高的。在缺少更多文献的情况下,王国维凭借个人见识与学识作出了这些论断。虽然囿于彼时文献稀少,王氏关于南戏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讹误与模糊——比如对早期南戏剧目的考证,王氏认为“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今天证明现存南戏最早者为南宋时期的《张协状元》——但无可否认,王国维为南戏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为近代早期关于南戏的研究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观点,开启了我国学者对南戏研究的先河。继王国维之后,对南戏相继展开系统研究的当推青木正儿、郑振铎、钱南扬、赵景深、周贻白、冯沅君、刘念兹等诸位先生。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中专设《南戏发达之径路》一节,系统分析阐述了南戏的源流脉络与体例特征。他认为“戏文”是与元杂剧相区别而言的,并非仅指狭义的温州戏:“此处所谓戏文者,当可解作周氏(周德清)指一种流行范围以南宋首都为中心之杂剧,非狭义的指温州戏一系焉明矣。”[15]35青木正儿继而从南戏之篇幅、乐曲编法、体例、舞台转换等四个方面与诸宫调对比,得出结论:“苟可推定南戏之改进,纯以诸宫调之刺激为主,则不必如王氏(王国维)之论,认为南宋时代具有与杂剧异其体例之戏文,发达而成南戏者。关于南戏之改进上,余发现一可视为温州人已着先鞭之文献。”[15]35
继王国维之后,我国较早将南戏纳入研究视野的当属郑振铎。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对南戏的起源、剧目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考证了包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在内的33种戏文的著录和残存情况,对南戏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应该说,郑振铎首次将向来为士大夫文人所鄙夷的南戏纳入文学史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其谋得一席之地,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南戏的重视与研究热潮,使“近年来(1930年代)研究中国古剧者,似乎对南戏有一种特殊兴趣。关于南戏各方面的研究,在报章杂志上间有专文论及,尤其是宋元南戏今存残文的搜辑,埋首工作者大有人在”。[11]180彼时,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以及陆侃如和冯沅君的《南戏拾遗》即为杰出代表。
钱南扬继《宋元南戏百一录》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陆续出版了《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以及《戏文概论》等南戏研究专著,“成为南戏研究的集大成者和20世纪南戏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16]早期,钱南扬以经史之学研究南戏,着意于南戏的辑佚、辨讹与校注;后期则将研究视角转向戏曲本体,对南戏的起源、剧本、内容、形式、演唱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就南戏名称而言,钱南扬认为“戏文”二字或为南戏正名,“南戏”或为“南曲戏文”的简称,而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应是地方之语。就南戏起源而言,钱南扬认为明代祝允明《猥谈》中的“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与徐渭《南词叙录》中的“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均有道理,继而创造性地提出了“酝酿期”的说法,认为南戏从温州当地的民间小调,经过酝酿期的发展,逐渐进入文人视野,后成为文人手中的作品。
“酝酿期”的说法,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被其后南戏研究的诸多学者所认同”。[16]就南戏剧目而言,钱南扬在参考《永乐大典目录》《南词叙录》《宦门子弟错立身》《太霞新奏》《按对大元九宫词谱格正全本还魂记词调》《顾曲杂言》等文献基础上,在其早期著作《宋元南戏百一录》中就辑得南戏102种,其中12种有全本流传,残本存曲流传者45种,完全佚失者亦45种。后来,又在其《宋元戏文辑佚》中进一步完善补充,辑得宋元戏文名目167种,其中有传本者16种,全佚者32种,有辑本者119种;辑得佚曲近900支,考订了123种戏文的本事,“是目前宋元南戏辑佚方面最为翔实的著作,也是南戏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巨著”。[16]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钱南扬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只是辑录南戏剧目与曲目,而是对所辑戏文的本事来源、流传情况、现存版本均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与钩沉。
与钱南扬同时或稍后,周贻白在其《中国戏剧史》中设《宋元南戏》专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中国戏剧历史上极有地位的南戏(即戏文),为了元代杂剧过分兴盛的缘故,反致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才发觉南戏的价值,在质量上并不比元剧相差多远。而其出生的年代,却还在元剧之前”,并且坚定地认为“南剧和戏文,本为一物而异称”。[11]131周贻白根据明代何元朗《四友斋丛说》“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剧为戏文”而得出“戏文……即南戏了”[11]131的结论,从戏曲发展史的视角肯定了南戏的奠基之功:“南戏源出北宋杂剧,首用代言体扮演故事,而奠定了中国的戏剧,这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情。”[11]140周贻白的戏剧史研究在彼时影响很大,赵景深撰文即言:“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17]
20世纪后期将南戏研究推向高潮,“引发各地学者将极大热情投入到南戏研究领域、推动南戏研究进入新局面的,是刘念兹先生与他的《南戏新证》”。[16]与钱南扬注重文献考证有所不同,刘念兹立足戏曲的本体属性,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结合互证的方法,将南戏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舞台艺术,对其民间性这一本质属性作了深度研究,也为南戏研究充实了新的研究方法。刘念兹以史料文献为基础,对受南戏影响较大的福建梨园戏、莆仙戏等流行的沿海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史互证,得出了福建梨园戏与莆仙戏是南戏重要遗存的结论。他认为,宋元南戏主要是民间的创作,刊刻付印的机会不多,遗留下来的剧本是很少的。目前只能从《永乐大典目录》《南词叙录》《宦门子弟错立身》《南九宫词谱》《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等文献中见到其名目。他根据上述文献资料,共辑得宋元南戏剧目244种,比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中的167种多了77种,另有明初南戏剧目125种,以及“福建遗存宋元南戏剧目”“福建遗存元明南戏剧目”和“福建南戏特有剧目”《荔枝记》与《荔镜记》等。关于南戏的起源,刘念兹先生在广泛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点说”,认为南戏的诞生地并非仅限温州,很可能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多地。此外,他在《南戏新证》中,还提出了南戏“五大声腔”说,认为“潮泉腔”是元末明初南戏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声腔,而明刊本《荔镜记》便是它的历史见证。这一学说引发了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学者们对南戏研究的极大热情,“直至21世纪的今天,很多学者仍沿着《南戏新证》的思路与方法,去发掘本地地方戏与南戏的传承关系,使南戏在当代研究的进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6]
继钱南扬与刘念兹之后,孙崇涛、俞为民、徐宏图等学者也对南戏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是1988年4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福建省文化厅在泉州、莆田联合举办了“南戏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南戏论集》,共辑集29篇论文,使南戏“更明显成为戏曲研究的热门话题”。[18]248
三、何以说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之所以认定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是基于南戏产生的时间点与逻辑性、受众的多元性与通俗性、流布空间的广泛性、演出剧目众多与体制完备、演出的在场性与民间狂欢性及对后世戏曲影响的广泛性与持久性等六大指标作出的判断。
(一)产生的时间点与逻辑性是南戏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座高峰的前提条件
南戏形成于两宋之间,早于元杂剧是不争的事实,业已成为学界定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10]239这是徐渭《南词叙录》的记载。祝允明的《猥谈》同样认为“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19]除此之外,元人刘一清在其《钱塘遗事》笔记中曾记载南宋贾似道(1213—1275)观看戏文的情形:“贾似道少时,佻挞尤甚。自入相后,犹微服闲行,或饮于伎。至戊辰己巳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20]可见,彼时南戏演出已然“盛行于都下”了。南戏早于元杂剧,在明人叶子奇的《草木子》里也可得到印证:“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其后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11]135从中不难看出,“南戏盛行”当在“北院本特盛”之前,不过,此后“南戏遂绝”则非实情。因为,元人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萧德祥……凡古文俱概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沈和……能词翰,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21]可见,元杂剧作家也是兼撰南戏的,且有南北合套的创体。所以,周贻白先生指出:“南戏于元极端发达之日,固未尝遽绝,其体制且仍为一般人所重视。不宁惟是,即南戏的声调,亦似未尝为元剧所掩。”[11]136张庚、郭汉城在《中国戏曲通史》中也写道:“元代南北统一后,南戏并没有因为南宋的灭亡而消亡,它仍然和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杂剧并行在南北剧坛上……南戏作家和艺人善于吸收各种养料来充实自己,因而到了元末明初之际,南戏便更加成熟。在创作上出现了新的高峰。”[22]209
就事物发展的逻辑规律而言,戏曲形成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由酝酿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嬗变过程。南戏由“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的村坊小曲到动辄几十出的鸿篇巨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衍变,其过程均有文献记载,有迹可循;而元杂剧“四折一楔子”“一人主唱”的体制似乎是遽然出现的。根据周贻白先生的考证,南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两朝的词和大曲,“唐宋大曲之用于舞蹈,至此有了着落,这是中国戏剧史演进的一条正路”。周氏认为,南戏可与诸宫调处于同等之地位:“南戏的渊源,大部分在唐宋人词。”“南戏是和‘诸宫调’站在同等的地位。不必说元剧,便是北曲的‘散套’,也当成为南戏的子侄行了。”[11]180此外,刘念兹先生通过田野考察,结合方志及禁戏材料等文献记载,抽丝剥茧,推测出在南宋时,漳州地区的戏剧活动便已十分盛行——这与徐渭《南词叙录》提及的“南戏始于宋光宗朝”的时间接近——继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南戏很可能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多地同时出现”的学说。曾永义也指出“‘戏文’或‘戏曲’是‘永嘉杂剧’又吸收说唱文学以丰富其故事情节和音乐曲调乃至曲调的联缀方法,从而壮大为‘大戏’,时间约为宋光宗绍熙间(1190—1194)”;同时,曾永义将“鹘伶声嗽”看作南戏的前身——“小戏”阶段,认为其形成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并将其形成时间推前到北宋仁宗至神宗之间(1023—1085);继而,曾氏又指出:“由于一些新资料的补充和发现,对于‘南曲戏文’发展过程中的‘永嘉杂剧’,其成立时间,起码应推前至北宋仁宗至神宗之间(1023—1085)。”[18]275由此可见,南戏完全符合从乡土民间长期酝酿到逐步发展,最终由文人染指而出现《琵琶记》等成熟之作的戏曲生成逻辑规律。
(二)受众的多元性与通俗性是判定戏曲艺术繁盛与否的关键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生产旨在创作有价值的艺术作品,而艺术消费则是这些作品得以发挥价值的途径。艺术生产决定艺术消费,反之,艺术消费也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艺术生产,可以激励艺术生产不断创新和发展。就戏曲艺术而言,其受众面的多元和广泛自然是其艺术生产繁盛与否的关键指标。元杂剧属于书会才人创作的戏剧样式,虽为场上之曲,但其文学性更强,且不说以王实甫、马致远、白朴为代表的文采派,更不用说以《王粲登楼》《杜甫游春》等颇具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文人抒情剧,即便是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本色派作家作品,也会因颇多丽藻华词、引经据典而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所不解,诚所谓曲高者必和寡。难怪清人梁廷枏在其《滕花亭曲话》中对元杂剧引用“经史”作出了批评:“《四书》语入曲,最难巧切,最难自然,惟元人每喜为之。《西厢》‘仁者能仁’等语,固属大谬不伦。马致远《荐福碑》云:‘我犹自不改其乐,后来便为官也富而无骄。’又云:‘谁似晏平仲善与人交。’……以上等语,几成笨伯矣。’”[23]可见戏曲中频繁引用“经籍”,很难讨好,观众自然不买账。
南戏无论是作家作品、题材类型、演出体例以及表演风格等,都与元杂剧有着显著的不同,呈现出更为鲜明的通俗性,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早期南戏根本没有明确的剧作家,多由乡土民间的艺人集体创作,是一种典型的草根艺术,纵使有一两个知道名姓的,其生平亦多不可考。诸如《赵贞女蔡二郎》《王魁》等早期南戏,则署名“永嘉人所作”。随着南戏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聚集在“书会”组织的职业剧作家,被称为“书会才人”,他们都是一些粗通文墨的下层文人,亦不乏小商人、郎中、算命先生、私塾先生等三教九流之士。诚如徐渭所言,“作者猥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10]240这些人地位不高,以编演剧本为生,与艺伎相依为命,只求戏班生意兴隆。可见南戏作家与市井观众之间的审美趣味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一点是迥异于元杂剧的。在题材方面,几乎有一半南戏表现的都是才子佳人抑或家庭伦理的爱情婚姻题材,这种情况和南戏进入城市以后得到发展,并且大量吸收了说唱、话本的故事题材有着直接关系,它们明显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城市人民在婚姻爱情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意识。在情节上,由于南戏不像北杂剧那样受“四折一楔子”结构的限制,篇幅可长可短,分出自由,可以灵活自由地像话本小说那样表现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充分满足了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就语言来讲,南戏在士大夫文人眼中似乎没有文辞可言,被视为“俚俗妄作”“村坊小曲”。不用说南戏的宾白,即便是唱词,也多是不加藻饰的白描。比如《张协状元》中净唱的《麻婆子》:
二月春光好,秧针细细抽。有时移步出田头,虼蚪儿无数水中游。婆婆旁前捞一碗,急忙去买油。(末白)买油作什么用?(净)买三十钱麻油,把虼蚪儿煎了吃大麦饭。[24]
这段景物描写充满浓郁的泥土气息,是最符合大众的语言。工丽和典雅的文章,虽可供案头的展玩,但在戏场上唱起来,对大多数的观众或者听众来说也是隔靴搔痒。
南戏的演出场所又多在勾栏瓦肆当中,与市井观众近乎零距离接触,因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此,余秋雨在其《中国戏剧史》中写道:
瓦舍的观众以市民为主,他们对演出的反馈,比宫廷中的观众更具有普遍性,比乡村间的观众更具有连贯性,这就为戏剧的成熟提供了一种既开放又稳定的气候。这些市民观众,文化素养比贵族文人低,社会见识比村野农民广,生活节奏和情感节奏都比这两种人快。他们的眼前,是拥挤的街市、繁密的船桅;他们的耳边,是如沸的人声、不绝的叫卖。因此,他们的感官已不很适应那种空灵、含蓄、蕴藉、悠远、缥缈的艺术形态,他们追寻着绵密而紧张的有趣故事、直接而丰富的感官享受。总之,这些瓦舍观众的市民口味,与戏剧的本性十分合拍。[25]65
(三)流布空间的广泛性是南戏旺盛生命力的鲜明特征
南戏,并非仅流布于温州,而是涵盖多地:向东南流播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一线;向北传到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直到元朝的京城大都;向西传播到江西、湖南、湖北。南戏流播地域之广泛,足以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彼时的兴盛。
如前所述,刘念兹就南戏的流布提出了“多点”说。通过对受南戏影响较大的福建梨园戏、莆仙戏进行实地考察,与史互证,刘念兹得出了福建梨园戏与莆仙戏是南戏重要遗存的结论,并论证了南戏很可能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多地“同时出现”的。此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就提到:“重要的是在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等古老的剧种中,还遗存了不少南戏剧目,有些至今还能演出……福建闽南一带流行的南音尚能演唱南戏的许多佚曲,《泉南指谱》辑存了它的许多唱段。”[22]213曾永义同样承认:“永嘉戏文或戏曲流入福建的可能性自然很大,这可从文献资料的蛛丝马迹和现存福建古剧来加以考察。”[18]263他通过引证刘念兹《南戏新证》辑得的宋元南戏与莆仙戏、梨园戏51个相同剧目进行分析,指出“凡此皆可见莆仙戏与梨园戏与宋元戏文的密切关系”。[18]267
及至元杂剧衰落之际,南戏依然以两条线索流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一条流布于城市,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较大,观众多为市民阶层,亦不乏士大夫文人;另一条则在江南的广大农村流行,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同野火烧不尽的离离之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到了明代,南戏的这两条支脉又孕育出了新的声腔。
(四)演出剧目众多与体制完备是评判南戏兴盛的核心指标
演出剧目众多表明南戏彼时的繁盛,体制完备则标示其艺术形态的成熟。众所周知,宋元南戏是源自民间的艺术,早期为集体创作,更多的是不见诸文字的口头表演,这和近代以来的地方戏曲早期演出的“路头戏”极为相似。即便后来一些粗通文墨的底层文人染指南戏,其剧本刊刻印制的机会也不多;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有意禁毁民间戏曲,更因为南渡之际,尤其是宋末元初之际战乱频仍,遗留下来的南戏剧本就更为稀少了。目前仅据《永乐大典目录》《南词叙录》《宦门子弟错立身》《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以及《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等文献,就辑录到180余种南戏剧目;据庄一拂1982年编著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可知,现存南戏剧本名目有210余种;另据刘念兹先生考证,宋元南戏剧目有244种。这些数据还仅仅是一千余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的,而那些消亡于历史烟尘中的,与彼时勾栏瓦舍、乡野民间演出的剧目,恐怕就更为可观了吧!
当然,在这众多剧目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有“南戏之祖”盛誉的《琵琶记》。此时的南戏早已不囿于南方,而是推广到了北方,呈现出复兴之势。诚如明人沈宠绥所言:“虽词人间踵其辙,然世换声移,作者渐寡,歌者寥寥,风声所变,北化为南,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竟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而词既南,凡腔调与字面俱南。”[26]今人亦认为,“《琵琶记》以其耀眼的光辉,不仅映照着当时的剧坛,而且笼罩着整部戏曲的历史。在元代,它是南北戏曲创作的殿军;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27]于此,足见“四大南戏”与《琵琶记》影响之巨大。
除此之外,颇值一提的是南戏目连戏。目连戏在民间经历了长期酝酿,直至发展到明代才真正勃兴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宋元南戏起到了关键作用。“明代目连戏的兴盛并非骤然勃起,在民间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出准备阶段,这就是宋元南戏。而元末南戏的复兴,对明代目连戏的兴盛更为关键,更为直接。”[28]40可见,明代目连戏“轰动村社”[29]的演出盛况,于元南戏已见端倪,是宋元南戏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成熟的戏曲”,[30]主要表现在其艺术体制的完备方面。产生于乡土民间的南戏,在其初期结构简单,形式活泼自由,角色不过三四人;但进入都市之后,南戏为迎合市民阶层的猎奇与求新的审美需求,广泛吸收诸宫调、唱赚、词调、宋杂剧、北杂剧的腔调、形式、表现方法和演出技巧,剧本开始因表现情节跌宕离奇、人物众多且关系复杂的故事而不断增长篇幅,剧中人物角色自然也随之增多,继而催生出了生、旦、净、丑、外、末、贴七种基本行当,形成了中国戏曲最早的完备的行当分配制度。据宋人陈淳给时任漳州知州的朱熹的《上傅寺丞论淫戏书》,我们不难推断这一过程的完成不会迟于南宋。在该文中,陈淳描述了“优人互凑诸乡保做淫戏”的场面,同时列出其八条“所关利害甚大”者。我们从“诱惑深闺妇女,出外动邪僻之思”“贪夫萌抢夺之奸”“后生逞斗殴之忿”“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州县一庭纷纷起狱讼之繁”[31]诸条中,不难发现彼时南戏演出的盛况,亦可揣摩其规模体制断非乡土小戏所堪比拟。“我们应该可以说,在南宋绍熙、庆元间,福建漳州已经有演员足以扮饰各色人物、情节复杂曲折、艺术形式已较完整、足以动人心魄的‘大戏’了。”[18]267早期南戏业已不局限于宋杂剧的三段体,更不停留于二小戏、三小戏的前戏曲时期,而是具有完整的长篇结构体制,甚至比“四折一楔子”的北杂剧之规模还要大上数倍。此外,南戏的“不叶宫调”与长短不拘、自由灵活的结构也成了民间戏曲的典型特征,而这恰恰为南戏无拘无束地讲述曲折动人的长篇故事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但降低了艺术接受者的门槛,也降低了艺术创造者的门槛,继而使得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的规模都空前扩大了。
(五)演出的在场性与民间狂欢性是戏曲评价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指标
如前所述,南戏既已成为体制完备、能够演出情节复杂离奇的长篇故事的剧种,那自然会诞生一批优秀的演员。遗憾的是,彼时那些无可胜计的、红极一时的演员早已随着历史风云而湮没无闻。即便如此,我们今天依然能从《青楼集》等文人笔记的字里行间寻觅出一些蛛丝马迹,既有像龙楼景、丹墀秀等“俱有姿色”“专攻南戏”的演员,又有像昆山张玉莲那样的,“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32]元代诗人杨维桢也在其《铁崖诗集》里称赞南戏女伶沈青青擅演南戏《破镜重圆》时云:“巫山薄雨随云散,女浦飞花逐山流。声传独如瑶草翠,才情浑似杜娘秋。”此外,还有南戏作家兼作演员的,比如史九敬先、刘一棒等,其中史九敬先以善扮喜剧角色著称。此时的南戏,和元杂剧一样,也出现了家族性的戏班。比如,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所写的戏班就是家族性的,王恩深、赵茜梅和王金榜是父女、母女关系。“在这种戏班里,除了主要演员之外,其他配角、伴奏人员以及前后台打杂,莫不是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动手。”[22]267
戏曲属于民间艺术,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游戏、娱乐、戏谑、传奇和狂欢,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戏曲也唯有在乡土的世界里,才能根深叶茂,枝叶扶疏。乡土的世界,离不开“土”,凡与乡土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精神层面的,往往都在前面著一“土”字,乡村戏台演的戏即称土台子戏。除乡土气息外,民间戏曲还具有浓郁的市井气,这是根植于农村的土戏进入城市后的必然选择——此时的戏曲开始作为艺术消费品,需要和市民阶层进行交换,所以必须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因此,乡土与市井又成为民间戏曲的共同属性,南戏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以戏曲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在观演过程中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狂欢。俄罗斯艺术理论家巴赫金曾概括出“狂欢”的四大特征:“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这种“无等级”“宣泄”“颠覆”显然是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精英文化格格不入的,是适合大众口味而与上层文化相对立的。“狂欢节类型的广场节庆活动、某些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等,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都是统一而完整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节文化的一部分和一分子。”[33]大众正是在观赏民间戏曲的狂欢中使郁积于心头的诸多不快得到了宣泄,从而获得了精神的愉悦。
南戏自形成伊始就颇富浓郁的民间色彩,演员与观众互动强烈,具有鲜明的在场性,这与其生成环境和自身艺术审美密切相关。温州繁荣的经济、壮大的市民群体成为南戏繁盛的温床。诚如钱南扬所说,“温州既是通商口岸,自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由于他们对文化的需求,当地的村坊小戏即被吸收到城市来。这种又新鲜又有生气的剧种——戏文,大为市民所欢迎,便在城市迅速的成长起来”。[34]对于城市和南戏之关系,余秋雨亦指出:“与紧邻朝廷的都市不同,这些地区(温州)的商市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自发的状态之中,市民生活更加灵活、散漫。”“这种在主流文化之外悄悄生长的南戏,是一种在形式上比较自由、在内容上比较轻柔的戏剧样式,与后来元杂剧的严整和高亢,形成鲜明的对照。”[25]83然而,正是因为其“新鲜又有生气”“灵活”和“散漫”的艺术审美,南戏才赢得了市民喜爱,使之狂欢。对此,不少文人笔记或诗词均有记载。比如南宋刘克庄就有不少诗句描写当时南戏在民间演出时的盛况:
《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二首》其一
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
山中一老眠初觉,棚上诸君闹未知。
游女归来坠一珥,邻翁看罢感牵丝。
可怜朴散非渠罪,薄俗如今几偃师。
《无题二首》其一
棚空众散足凄凉,昨日人趋似堵墙。
儿女不知时事变,相呼入市看新场。
另如:“巫祝欢言岁事详,丛祠十里箫鼓忙。”(《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二首》其二)“不与贤豪竞华毂,且随儿女看优棚。”(《灯夕二首》其一)“陌头侠少行歌呼,方演东晋谈西都。哇淫奇响荡众志,澜翻辨吻矜群愚。”(《再和》)“抽簪脱袴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即事三首》其一)①
此外,宋人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淫戏书》中更是描述了彼时南戏演出的空前盛况:“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聚敛财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翠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31]至于南宋目连戏在民间的演出,我们从“无奈愚民佞佛,凡百又九折,以三日夜演之,轰动村社”“竟夜不能寐”这些只言片语中便足以窥见其壮观火爆之势。民间是中国戏曲扎根的土壤,民间演戏的火爆炽烈表明孕育戏曲的土壤肥沃膏腴,更证实了戏曲发展的根深叶茂。
(六)对后世戏曲影响的广泛性与持久性树立了南戏在中国戏曲史中的基本坐标,是评判南戏地位和价值的又一关键指标
明代吕天成在《曲品·自序》中“归检论评,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35]其中列入“旧传奇”者,始于南戏《琵琶记》,以至于嘉靖前之作品;列入“新传奇”者,则皆在嘉靖水磨调形成之后。由此可见,吕天成认为从南戏至明清传奇是一脉相承的。据此,今人曾永义指出,吕天成所谓“旧传奇”,可认为是“新南戏”“实质上正是由宋元南戏过渡到明清传奇的产物”。[18]393至于南戏对明代四大声腔的影响就更为直接了。南戏是孕育明清传奇的母体,这已成学界共识,自不必赘述。明代四大声腔中,昆曲影响最大,对后世京剧及地方戏而言有“百戏之祖”的赞誉;那么,就辈分而言,南戏恐怕就是“百戏之祖”的前辈了。至于弋阳腔一脉则开启了后世高腔花部诸腔的先河。不惟明代四大声腔,南戏还对长期扎根于民间的目连戏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今天流传的一些剧本,如莆仙戏《目连救母》、江西南戏《目连救母》等,“都保留了早期南戏的形态”。[28]41更重要的是,南戏还影响了中国戏曲的整体美学风格。扎根于民间的南戏和进入大都市、受到文人染指的南戏形成了一雅一俗双线传承路径,奠定了中国戏曲雅俗共赏的基本特质和多元统一的艺术风貌,时至今日,京昆的典雅精致与地方戏的质朴通俗无不受其影响。
结语
南戏,作为最早成熟的中国戏曲样式,充分吸收了宋杂剧、金元本和诸宫调等同时期姊妹艺术的养料,由民间歌谣、小戏逐步发展成为篇幅不拘长短、形式灵活自由、表演质朴自然、体制行当完备的大戏,且由东南一隅迅速传播,南下北上,东进西突,流布八方,时至今日,不少剧种剧目依然有南戏遗音活态传承;南戏剧目众多,既有高原,又有高峰,更多烟火气十足的质朴之作,丝毫不逊色于北杂剧;南戏不乏名伶,只因历史条件所限,多湮没无闻;南戏自始至终保留着民间戏曲质朴自然、鲜活生动的艺术本色,并持久影响着此后中国戏曲的基本审美追求;南戏始终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血脉相连,艺术地讲述着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并与之形成精神上的高度狂欢,因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奠定了此后中华戏曲的优秀传统,成为中华戏曲经久不衰、薪火相传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笃定地说,南戏形成了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注释
①以上诗句,均引自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第197、220、97页。
参考文献
[1]郑传寅.中国戏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9:2.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叶长海,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91.
[4]廖奔.金世宗、章宗时期河东杂剧的兴起:晋南金代戏曲文物考索之一[J].中华戏曲,1986(2):5-31.
[5]吕薇芬.录鬼簿的历史地位[J].戏曲研究,1986(26):78-103.
[6]麻国钧,等.剧种·剧目·剧人:中国传统戏曲知识简介[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23.
[7]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8]杜桂萍.文体形态、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明清文学研究行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6.
[9]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5.
[10]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1]周贻白.中国戏剧史 中国剧场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12]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M].于允,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2.
[13]张燕瑾.中国戏曲史论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24.
[14]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1.
[15]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M].王古鲁,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16]刘祯,韩郁涛.20世纪南戏研究及方法:从钱南扬到刘念兹[J].艺术学研究,2019(2):76-87.
[17]赵景深.俗文学[N].中央日报副刊,1947-07-18(10).
[18]曾永义.戏曲剧种演进史考述[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
[19]祝允明.猥谈[M]//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篇: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226.
[20]刘一清.钱塘遗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000.
[21]钟嗣成.录鬼簿[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21.
[2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23]梁廷枏.曲话[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八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61.
[24]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4.
[25]余秋雨.中国戏剧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26]沈宠绥.度曲须知[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五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8.
[27]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80.
[28]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1997.
[29]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14.
[30]《中国戏曲史》编写组.中国戏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68.
[31]陈淳.北溪大全集:上傅寺丞论淫戏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10.
[32]夏庭芝.青楼集[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23.
[33]诹访春雄.日本的祭祀与艺能:取自亚洲的角度[M].凌云凤,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35.
[34]钱南扬.戏文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
[35]吕天成.曲品:自序[M]//中国戏曲研究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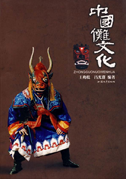
2025-11-06